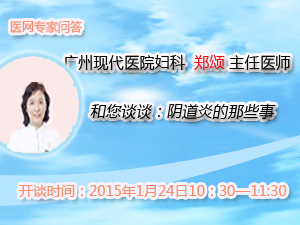新贵:时代精英的圈子生活
- 2007/4/27 来源:
- 相关内容
医网摘要:
其实圈子根本不是一个组织。就像一个名人与另一个名人相遇时,他们是否同属一个圈子只是心照不宣而已。共同的利益、地位、兴趣、人际交往可以构成圈子,却无法保证一定会使你产生归属感。 在竹林里
在竹林里
“竹林七贤”,还是“竹林七闲”?反正是那个时代7个找不到工作的人,在今天河南某一块地方找了一片竹林开小会,主要议程是喝酒,醉了就卧倒,或者做瑜伽。
据说那时还流行吃一种“七步散”,那玩艺儿很厉害,吃了就东倒西歪,产生幻觉,有点像摇头丸。
古代人的名片上大概都印着出生地,好像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竹林七贤的时候,还要这样说:谯国嵇康、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琅邪王戎。这几位在所谓竹林中盘踞了多少时日现今已不可考,但是后来进入传说,就把这件事弄得神乎其神,事实上,魏晋时代的人也是人,除了生活节奏慢一些,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那时候交通不便,所以相聚不太容易,本来是几个当时的小名人在一起喝酒,传出来就成了一件很风雅的事。而这事是他们7个中谁说出去的,谁又加以改编,想达到什么目的,就很难说得清了。反正这个小圈子很是了得,音乐家、作家、政府官员各种角色都有,考虑到当时乃至1600年来恶劣的生存环境,也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人们会向往这种小型聚会了。
晋代人喜欢谈论老庄,同时也不放弃儒术,也就是在社会与自然中间摇摆。这7个人大小都当过几天官,而且全都是诗人,也全都是酒腻子,喝多了就会乱来,很像今天的行为艺术。嵇中散、阮步兵和阮咸都懂音乐,现在民乐方面有一种乐器叫大阮中阮小阮的,就是因为阮咸会弹这个,拿他来命名的。王戎在里边官最大,相当于国务委员,但是人品最差,他家的李子拿出去卖之前,他都要挨个把核打个洞,让别人没法种。刘伶和阮籍酒量最大,刘一提起酒来就像尼采看见阿波罗一样激动,而阮有点黑色幽默,在别人晒书的时候他偏要晒他的裤头。向秀和山涛相对正常一些,属于诗人里边不爱闹事的。说来说去,就是这么一群人,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私人行为,被我们称作“竹林七贤”,或者“竹林七闲”。竹林在河南,因那时首都是洛阳,当然,那时的河南人不是今天的河南人,因为后来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,就把这些河南人打跑了,他们一口气跑过长江,而首都洛阳就慢慢变成了一座可怕的空城,“竹林七贤”的故事,也就没有河南人的份了。因为河南人到了江南,找到了新的竹林,形成了新的圈子,他们当然也不再是河南人,而应该是江南人。这是后话。这段历史说明,圈子是变动不居的,哪里有闲人,哪里才有圈子。如果这世上连闲人都忙着逃难,圈子就该解散了。 东林党人
东林党人
大概在明朝万历时候,一个叫顾宪成的人办了一所东林书院,与当时混不上官做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堂设座,每岁一大会,每月一小会,讲正气、讲学习。当时人叫他们东林党,其实当然不是一个党,而是一个学校嘛。为什么要叫党呢?孔子说,“君子群而不党”。可见党是一种不好的叫法,意思就是,一帮小人,搞在了一起。
当然中国话的意思是时时在变的。比如奢侈现在就是一个挺受用的词儿,而以前是用来批评人的。这并不是说中国话没有原则,而是太有弹性了,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词能这样千变万化,直到现在还需要反复修订词汇的意义。所以东林党,显然是一些不喜欢他们的人的叫法。就像印象派,一开始也是讽刺的意思,后来竟成了流派的代称。
明朝政治是黑暗的,得意的是太监们,倒霉的是老实人。东林党里边的人全都在黑名单上,看谁不顺眼,拿名单出来过一下,找个罪名就干掉了。所以,敢做东林党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。
其实不光明朝,很多时代都有所谓朋党。东汉、晚唐、北宋,其时政治情形大多不明朗,人以群分,排挞异己,而结果是终于两败俱伤。
当然,东林党的名声还是好的。这个小圈子一度控制了中央直属机关,当时的首辅刘一景、叶向高,吏部尚书赵南星、礼部尚书孙慎行、兵部尚书熊廷弼,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,但当时社会已无正义可言,皇帝又都不中用,所以即使有好的想法,也要看合适的时机和环境才能见效,否则就只是在一个小圈子内,自己悲壮一把。
东林诸人后来大多遇害,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就如梦幻泡影般消散。紧接着满清入关,为日后中国的电视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,历史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刺性,这说明人们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有时并不一致。像清末康有为,也有一个类似东林党的小圈子,以为自己能挽狂澜于既倒,其实早知狂澜既倒,哪如顺水推舟。 城市之光
城市之光
中国在20、30年代,开始有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北京和南京虽然也都是中心,但只有上海做到了真正与国际接轨,资本家和买办阶层,失意的证券经纪人与舞小姐,在野政党领袖以及吃斋的督军,影视明星伴着面粉大王,青帮头子伙同秘密警察,这些花色各异的人群就生活在一座城市里,彼此交通或互不相扰,当然,一个个小圈子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。
鲁迅大约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团结别人的人,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周围总有一群朋友,虽然他不以领袖自居,但也无意改变他作为一个圈子核心的状况。人有了名气就会有各种麻烦,所以鲁迅身边的人,给他带来麻烦的也不在少数。他的杂文中总有若干与某某文人反目成骂的记载,当然那时的人没什么法治观念,不至于挨了骂就闹到法庭上,最多再写一篇文章骂回去就是了,这样你来我往,报纸才有看头,直到某一方骂倦了,先行住嘴为止。鲁迅也并非得理不饶人,一定要痛打落水狗的,但是他的脾气似乎很不好,往往结了文怨,在朋友请客说和的酒桌上却又再度翻脸。所以那时的作家们委实对他不大喜欢,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地位,所以只好在文字间冷嘲热讽,也许不少人喜欢看鲁迅被激怒的样子——人在潜意识里都是很变态的。可惜在他逝世之后,上海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给大家骂了,因为又打仗了,大家都忙着逃难,就像当年的河南人一样,拖家带口从东部向西南一路小跑,重庆、昆明成了后方重镇,喘息稍定,圈子又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,因为这次不是八王之乱,而是外敌入侵,大家就可以不必像没头苍蝇一样各顾各,而不相熟的人在险境中相遇,新的圈子就有可能诞生,更不用提原本就是好朋友的,在外就更加相互需要了。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聚在林徽因客厅里的时日竟比战前还多,而像黄苗子和郁风这样的年轻人也能在重庆找到自己的小圈子,他们与叶浅予等自嘲都是二流角色,还为小圈子起了名字叫“二流堂”。如此等等。
和现在不同的是,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中西兼收,又加之国家困顿,在客观上激励人们有所作为,因而一时人物,尽出其中,这些人际圈的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资源,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整合,一群英才整合在一起,八仙过海一般,不仅形式上好看,而且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。 在大院里
在大院里
“红色贵族”这个词,既不流行,也未落伍,它特指某一类人,也就是所谓的干部子弟。但是有一点要说明,干部的孩子不等于“干部子弟”——通常,父母应是行政13级以上,或有“厅局级”以上的待遇(部队应为师级),才能够算“干部子弟”,称得上“红色贵族”。他们造就的“圈子”,在中国近50年间的社会舞台上虽不能算举足轻重,但也足够引人注目。
北京为数众多的党、政、军各部门,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,就已纷纷在北京“皇城”外围“圈”得一块地,盖起了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,加上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,再有森严的门卫,里面是一个“小社会”,工作区,家属区,娱乐体育场所等一应俱全。北京西郊大部分是军队“大院”,有“空军大院”,“海军大院”,“总后大院”等军事单位。三里河与和平里一带则是国务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。占据北京最好地理位置的“大院”当属位于景山后面的总参“地安门大院”和沙滩后街的文化部“大院”,以及位于府右街南口的统战部“大院”。这些“大院”里面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。
文革前,“红色贵族”们大体集中在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几所中学里面。海淀区有北京一零一中学、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八一中学、育英中学、“十·一”学校等。西城区有景山学校(也许是东城区)、男四中、男六中、男八中、北京女一中、北京师大女附中等。这里面名气更大一点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、北京男四中、八一中学和景山学校。现今中国部级以上官员来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京男四中的人不少。八一中学集中了军队干部子弟。景山学校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一所直接领导的学校,中央直属机关的许多干部子弟都就读于这所学校。
由于“红色贵族”相对集中,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20世纪60年代,学生们常能准确地知道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,他们我行我素,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,以精英自居。现在看来,那时“红色贵族”们的政治见解也就是“语不惊人,死不休”,并无什么独到和高超的地方。这些不满18岁的孩子们有着颐指气使,舍我其谁的“霸气”,而在文革期间,当他们的父母们被“打翻在地”时,他们敢于反抗,矛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“中央文革”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红色贵族”们的少年血性已经不再。没有人怀疑,他们或早或迟地都会成为政治和商业上具有优先权的人。他们在狂热的政治风潮中算是首当其冲,有的风光,有的失意。而在80年代之后,他们也都纷纷实现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成功。当然,在一切行事都要强调“低调”的今天,他们身上“红色贵族”的光芒已然不再,安逸富足的生活和享受内心的平静成了惟一的主旋律。成年后的他们,大部分变得平淡且能豁达地看待周围世界的变化,然而他们的精英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。 技术时代
技术时代
差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,热闹了一阵的知识界开始失落,人们转向更为实际的层面,一些人丢掉了操作性不强的社会理想,一些人流亡海外,原来的圈子也就似乎解体了。在20世纪80年代,这些风雅而略显土气的圈子曾是年轻人向往的地带,但是它们显然无助于现实。而对现实感到失望,几乎是那时的一种病症。
写过《你别无选择》的刘索拉以音乐之名,在美国浪荡了10年左右之后,带着她的东方蓝调回到北京。显然,北京已经不是她梦想过蓝天绿海的那座城市了,但她依然能找到自己圈子的痕迹。和洪晃等人一样,刘在798厂区的日常生活既远离北京,又深入其中。而洪不仅在杂志圈如鱼得水,甚至还是个社交明星,刘形容她大脑转速飞快,口若悬河,这位有个著名母亲的“红色贵族”如今已站在社会前排,而她们的圈子也呈现出纵横捭阖的状态,圈子虽然仍为少数人分享,但不再封闭,就像同样在美国住了10年的艾未未,自从他在京顺路边草场地盖起了自己那幢像盒子一样的大屋之后,进出的人不仅有马未都这样的古玩收藏家,也有王朔、张元、姜文一类的作家导演,至于画家、诗人、行为艺术家,中国外国的媒体,更是不在话下。圈子这种开放而不稳定的状态,颇与当下的时代特性吻合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各种圈子按照职业特征,仍旧是相互独立的,但它们又都处在同一个大平台上,就像有人说整个世界是建立在一只乌龟背上的一样,没有人能看到那只乌龟,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它。
谁能想到,脱离了理想主义的幼稚病阶段,却迎来了人际关系的技术化时代。
编辑:朱磊
本文来源: http://man.ewsos.com/a/20070427/36010.html